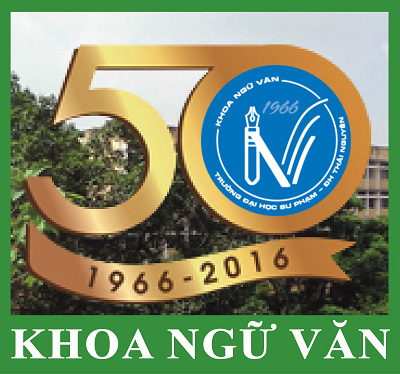Nguyễn Cẩm Anh
摘要:陈子昂是中国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所主张的“兴寄”、“风骨”等革新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六朝到唐初诗歌创作方面注重形式主义、艳丽纤弱的诗风,同时陈在新理论的指导下艰苦创作、努力实践,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为唐代诗歌的革新与健康发展作出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陈子昂 诗歌 革新
唐代是中国文学、特别在诗歌方面不断地发展并取得很多出色成就的时期。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诗歌精华,而且由于唐代开放的风气、清明的政治以及统治者的推崇,使唐代诗歌有了长足的跃进。随着文学与诗歌的发展,文学批评也进一步发展,很多重要的文学主张在这时期相继出现,为繁荣唐诗作出重要的贡献,其中陈子昂的“风骨论”和“兴寄论”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陈是唐代第一位从美学意义上批判南朝诗并提出诗歌革新的作家,也是唐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对于陈子昂诗歌的革新思想研究也出现很多不同的意见。在论文的框架内,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去分析陈子昂的诗歌革新思想及其创作实践。
一、陈子昂的诗歌思想:复而变
陈子昂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和主张,是顺应唐初诗坛变革六朝诗风的要求而提出的。初唐诗坛仍沿袭六朝的作风,在审美这方面十分注意文辞的声色之美,题材以歌德颂圣、歌舞升平的应制为主。在这样情况下,陈子昂站起来呼吁诗歌革新,提出了“风骨论”与“兴寄论”的文学创作主张,要救诗歌中应该有充实的内容、高尚的情感、语言朴素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是以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为纲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表达自己对诗歌革新的思想:“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逶迤颓靡,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音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1]
在唐诗发展的历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这篇文章集中体现陈子昂对艺术审美的观点,他反对六朝诗坛无病呻吟的透逸颓靡、美丽而无感的文风,并且要救学习汉魏诗歌的优良风貌,强调“风骨”[2]与“兴寄”[3]。
实际上,陈子昂之前,在一些理论作品当中曾有作者提及到“风骨”和“兴寄”。早在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就有《风骨》、《比兴》两篇专论,钟嵘的《诗品》也论及“风骨”、“比兴”问题,而且这两个作者的专论都是用以批评形式主义文风的。据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载:“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而且杨炯、卢照邻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时也都提到了风骨问题。从上面《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那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陈子昂把“文章道弊”的时间定位在晋宋以来的五百年。然后,他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就是批评内容空泛、风格浮艳的文风。接着,他在继承“风雅”[4]、“汉魏风骨”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兴寄”说。陈子昂是崇尚“比兴”的,他在《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中曾说:“夫诗可以比兴,不言易著?”[5]。这就是陈“兴寄”说的内容,就这样,他就把历来多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的内容的基本要求:感发意兴,遣兴抒怀,有感而作,有情而发,作而有所寄托。陈子昂还标举“汉魏风骨”。由于汉魏之际以三曹父子为领袖、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风骨峻嶒,文气慷慨,所以深受后人的推崇。初唐诗社会文学等发展的盛期,陈子昂认为创作作品需要带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在创作方面要有创新,同时也要继承传统创作风格的优秀之处,陈子昂的理论主张正是适应了这种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他提出诗歌需要高扬慷慨磊落的“汉魏风骨”。他之所以要继承“风雅”、“风骨”等理论是因为他想借助这些理论的正统性、经典性来增强其理论主张的号召力和批判力,以扫荡诗坛无病呻吟的透逸颓靡之风。表面看来,他似乎是在崇尚复古,所以,不少学者认为陈子昂的主张主要是复古,复多变少,但是,仔细分析这段话后,我们不难发现,陈的理论主张虽然不是完全否定汉魏六朝文学的积极因素,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有所突破,这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实质上是复而变。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者对陈子昂的“风骨”和“兴寄”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许总认为:“以虚拟之物托寓内心真情的方式是“兴寄”的典型形态,昂扬的基调与阔大的襟怀,是“风骨”最本质的特征,以物寓义与直抒襟抱是“兴寄”与“风骨”表现的最基本的两种方式。”[6]张采民认为,陈子昂提出的“兴寄说”:“既包含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包含寄托讽喻之义,‘兴’是为寄托服务的”,它把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的整体要求。提倡“风雅之道”就是“主张诗歌创作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要干预社会,干预政治”[7]张侃认为:“与刘勰、钟嵘相比照,陈子昂的“风骨”说已吸收了齐梁以来对诗歌辞采声律等方面的探索成就,与汉魏“风骨”相较,在慷慨苍凉、浓郁跌宕、笔调爽朗精健而外,没有了那种感伤的情调,而为豪放,为悲壮,为昂扬壮大......陈子昂的“兴寄”说,是从《诗大序》的“美刺比兴”发展而来,即要求作品要有实际内容,表现出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8]但从总体上来讲,通过上述的分析与举证,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陈子昂在文学主张上有一定的复古主义倾向,但这种“复古”就是继续吸收汉魏六朝文学的积极因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有所突破,这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实质上是复而变。同时,跟陈同一时代文人的主张进行比较时(比如:上官仪所创建了“六对”、“八对”的诗歌律化,根本只是改变诗歌的形式,而内容方面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陈子昂的文学理论的革新与突破,他强调的是反映现实、内容充实、风骨刚健、气势雄盛的诗文。他也是第一个把“风骨”与“兴寄”二者结合起来,使诗歌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逐步达到统一,完整的创新境界。因此,可以肯定,陈的这种革新思想对唐诗的盛行功不可没。
二、从思想理论到创作实践
针对初唐文学的现状,陈子昂呼唤诗歌创作需要革新,并往往把这种革新主张运用到他所创作的作品里去。陈子昂一生创作的作品不是很多的,统计资料表明,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陈子昂的诗,实际上也只有一百二十七首[9]。但从他的作品分析后,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陈子昂已经确实把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陈的《感遇》三十八篇、《登幽州台歌》等代表性作品具有切实的内容、刚健形象的风格,已经充分证明他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当运用的作品创作时使得作品充满活力、蓬勃生气、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讨人喜欢和赞赏。
陈子昂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纯正的思想、刚健、清新的文风和丰富多彩的内容等特点。只要拜读他的三十八篇《感遇》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内容,或感慨时事,或咏史咏物,或言情抒怀,或歌赞山河,或送友赠别等等,这一特点跟初唐诸家单一的描写对象与传统内容相比,真是大大的区别。当时文学盛行的都是贵族文学。美女妖姬、王公贵戚、池榭楼台、风花雪月等是诗人歌咏的主要对象。但陈子昂诗歌的内涵已经改变了。他的诗歌对象也很丰富,具有社会性。首先,对于陈子昂来说,广大人民的苦难是诗歌最重要的反映对象。从社会的现实出发,诗人所表现出的是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感以及为他们而斗争的笔意。比如在《感遇》(二十九)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的镇压,给广大军民带来的灾难: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
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
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
拳跼兢万仞,崩危走九冥。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
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10]
有时陈借古喻今,寄托了诗人报国的志愿和报国无门的感慨,充分体现了诗人比兴寄托的诗歌主张,如《感遇》(四):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11]
从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角度出发,陈子昂勇敢讥讽朝政,抨击了上层封建集团的腐败与残酷:有时形象地刻画了官僚政客们的丑恶嘴脸(《感遇》十),或深刻地批判统治集团的荒淫享乐、奢侈浪费(《感遇》二十八),或反映了初唐宫廷的激烈斗争(《感遇》十五),有时还突出地揭露了任人唯亲的朝政,即统治者宠信投机的小人,轻待为国效力的有功之臣的现象(《感遇》十六、十八)。读了《感遇》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其政治色彩特浓,陈子昂就这样用诗笔经常自觉地干预政治的诗人,用诗歌来直接讥讽当时的朝挺,可说初唐近百年间,陈子昂是先锋的一个,也是同一时代非常罕见的一个。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子昂的《感遇》在继承前人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成功地将个人的志向、感慨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对人生宇宙的思索结合在一起,为古诗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内容,这些都是陈子昂古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对汉魏古诗的“复”和“变”。
但是,陈子昂在诗歌天地中也体现出他的美好思想和高尚情操。但有时面对黑暗和污浊的社会,这些善良的理想与实现又变成一种矛盾,并造成他的悲剧。《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孤独心灵的声音: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短短的四句诗,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对幽州台的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继承“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重大作用。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篇幅非常之短,却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诗的前三句以浩茫宽广的宇宙天地和悲伤沧桑易变的古今人事作为背景加以衬托。最后一句才是关键,其充满抒情,使得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也正因为在悲怆的深层,蕴藏着一股积极奋发欲有所作为的不甘命运摆布的豪气,才能在千载以下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正是陈创作实践的创新,也是前所未有的创新。
众所周知,理论是由其实践内容来反映的,要更深层次的探讨陈子昂诗歌理论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必须结合陈子昂本人的诗作来加以研究。那么,分析陈的作品后,我们看到陈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基本上已恢复了前一代文学的精神,也看到他所提倡的革新理论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能给当时文学和诗歌创作带来一股新的生气。换句话说,陈子昂已经很好地把他的理论运用到创作过程中去,很好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达到预期的效果。正是在陈的理论的影响力下,陈以后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代有名诗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收其的观点,并且不断地去补充、发展并完善,构建成唐诗的整体精神和理论系统。因此,陈子昂革新理论可视为一条继承古人思想、革新、发展并流转到后世的伟大桥梁,从此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发挥不可否定的作用。
[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9)
[2] 所谓“风骨”主要指诗文内容充实,情调慷慨,风骨崚嶒,语言刚健
[3] 所谓“兴寄”主要指强调感情的兴发,并以委婉形象的表现手法,寄托讽喻之义的的创作艺术
[4] “风雅”、“比兴”是《诗经》“六义”的主要内容。
[5]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903)
[6] 徐总.风骨兴寄的实践成果及其渊源影响——陈子昂诗论[J].中国韵文学刊,1994(2)
[7] 张菜民.论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与诗歌创作[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1998(4)
[8] 张侃.陈子昂《修竹篇序》的诗歌主张再评论[J].兰州大学学报,2000(3)
[9] 吴珮珠.诗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J].思想战线,1987(1)
[10]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893)
[11]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818)